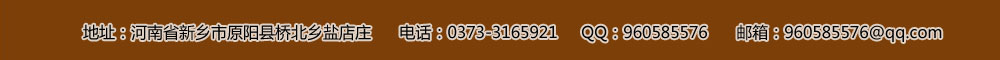40医生的修炼不可思议的预感4
近几年,我们发现自己在治疗病人时经常出错。出错率这么高,真让人沮丧。有时,我们明明知道如何做才是正确的,但还是会出现差错,我们就这样不断地重蹈覆辙。如今,我们已经开始明白,经验可能会误导我们,技术可能发生失误,另外自身能力不足也是个问题,这些都可能造成误诊。
还有,知识和实践之间是有差别的。比如,我们知道用阿司匹林可以治疗心脏病人,而如果配合抗凝血剂一起服用,效果会更好。但是,在心脏病发作的病人当中,有1/4的病人并没能得到阿司匹林,而且有一半的病人应该使用抗凝血剂,但医生却没有开。
总体上说,在美国,医生在救治病人的时候,有八成以上的治疗是按规定进行的,但是在有些地方,这个比例还不到两成。医疗规范在很多地区仍有待加强,只有加强监管,才能督促医生按照规定去医治病人。
但是,如果你身在医学界这个圈子里,或者有直接接触病人的经历,就不难发现一个更巨大、更显而易见而且更无奈的困难,那就是在医疗诊断中有太多未知的可能性。医学中有大片的灰色地带,每天我们都会徘徊于这些地带中,就像对爱丽丝这样的病人,我们不能肯定病因,因此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如何做,但最终我们不得不做出决定。
比如,我们发现病人得了肺炎,那么是该让他住院呢还是让他回家?背痛是要手术还是用保守疗法?病人皮肤出现红疹,哪种红疹要手术,哪种注射抗生素就行?对数不清的病例,我们都找不到明确的答案。还有很多情况,我们不知道要如何去做。
曾经有一个专家小组对现实的医疗案例进行过分析调查,以三类病例为例,结果发现有1/4接受子宫切除的病人、1/3接受耳膜穿孔修复手术的儿童和1/3植入起搏器的病人在手术后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也就是说,手术对这些病人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没有可依据的规则和范例,于是你只好开始跟着感觉走,凭自己的第六感来做决定。有时,你可以靠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但难免还是会陷入迷惑。
§§§§
在遇到爱丽丝的几周之前,我诊治过一个老太太。她已经90多岁了,常年被风湿病困扰。这次她来看病是因为腹部剧痛,甚至连背部也伴有疼痛。我从她口中了解到,她之前的主治医生在不久前发现她腹部有颗主动脉瘤,我立刻警惕起来。
我小心翼翼地为她检查,发现她腹部有一块很大的不明物,软软的,还会滑动。迄今为止,老太太的脉搏、血压、体温等还算稳定,但我可以肯定那颗主动脉瘤随时都有可能破,前来会诊的血管外科医生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告诉老太太,要想保命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马上动手术。我们向她解释,这是一台大手术,而且恢复的过程比较漫长,术后可能要在特护病房躺很久。
出院后,她需要别人照顾,以后可能必须和孩子住在一起(现在她是一个人住);另外,手术风险也很高,由于她的肾脏功能不太好,死亡率至少有10%~20%。老太太不知道要如何决定,于是我们请她和家人好好商量一下,15分钟后我们再回来听取他们的决定。
结果,老太太说,她不想手术,只想回家。她说,她已经活得够久了,一直以来都体弱多病,她自己也知道时日不多,遗嘱也都拟好了。老太太的亲人们都十分伤心,但她语气坚定,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我开了一些止痛药给她,30分钟后,老太太就回家了。我想,她命在旦夕。
几周后,我给她儿子打了电话,想问问她怎么样了,或者丧事办妥了没?出乎我的意料,接电话的正是那位老太太。我吃了一惊,有些口吃地向她问好。她回答道,谢谢你,我很好。一年以后,我听说她过得不错,依旧独自一人住。
§§§§
根据30年来神经心理学的研究,人类的判断就像是记忆力和听力一样,常常会出现错误。我们可能高估了危险性,习惯因偱守旧,太大的信息量令我们应接不暇,自身的欲望和情感因素以及事情发生的时间的影响也都会干扰我们的判断。
此外,信息出现的顺序和问题形成的方式也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训练和经验可以帮我们避免这些错误、化险为夷,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经不起研究人员通过显微镜的审视。
很多研究表明,医生的判断存在偏差。比如,弗吉尼亚医学院在一项调查研究中发现,医生为发烧的病人做血常规时经常高估其感染的可能性,有时甚至高出4~10倍,如果医生近期还诊治过其他血液病人,这一比例将更高。
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医疗中也存在沃比根湖效应[2],大多数医生认为自己诊治病人的死亡率应该比平均值低。俄亥俄大学和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以医疗决定的正确性与医生对自己所下判断的信心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太大联系。对自己的判断信心十足的医生和没有信心的医生相比,其医疗判断错误的概率基本一致。
对临床医疗决定有深入研究的医学专家戴维·埃迪回顾了一下十几年前《美国医学会杂志》刊载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的一些数据,痛心疾首地给出了一个结论:“医生做的很多决定其实没有任何根据,也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变幻莫测。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种不合理的决定对有些病人的治疗并无益处,甚至有越治越糟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