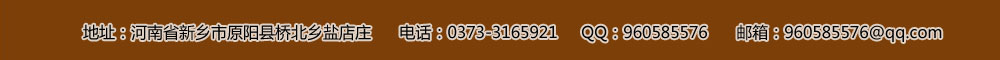我看的各国病人医疗的文化差异
门诊的时候,医生和患者的沟通往往建立在各自的生活体验之上。每次和患儿家长见面,我的医学经验和人文体验都得到了丰富,我相信来访的家长也有同样的体会。在这一节,我试图还原我和患儿家长日常互动的某些场景,现实中医患的交流往往决定了治疗的下一步。
我记得在一个国际医学研讨会上,有一个主题演讲说的是欧洲抗生素使用的地理差异。主讲者用标色地图来表示不同地区的抗生素消耗量。从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南北梯度线,表明南方地区比北方地区耗费更多的抗生素。但是,人们没有找到什么医学上的原因来合理解释这一现象。比如,是不是因为南方地区传染病更多,所以抗生素量更大?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南北的文化差异,病人是这样,医生亦如此:北方病人在用抗生素之前,能够等待更长的时间,北方医生也是这样,在开处方时,他们更为小心谨慎。当然这是总体趋势,在个人层面上总会有例外。
我就有过类似的体验,来我这(在北京时)看病的一些德国或欧洲北部的父母,在对待治疗中耳炎问题的时候,能够接受不用抗生素的治疗建议;或者在医学允许的范围内,至少先试着不用抗生素。
这种态度也同样表现在发热时用不用退烧药的情况,北欧的一些家长认为退烧药往往会延长疾病周期,事实上的确有科学研究表明服用退烧药会延长感冒时间。
在现实生活中,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医疗文化,每个国家的医学发展史不同,每个人如何从自己所在的医疗体系里成长、如何处理健康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
中国的时下现状是,大多数患者只有极少的时间和医生沟通。我认为这是医疗体系构架不合理造成的,也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后一种解释最为常见),这种现状毫无疑问影响患者就医的状态。
第一次来见我的家长往往着急得很,他们想在几分钟内解决小家伙的所有问题,包括开处方。他们迫不及待地把孩子送到我面前,几乎要塞到我怀里,不要把孩子放在诊查桌上,恨不得我坐在椅子上就开始检查,然后他们想让我赶紧写处方,这样全家人好赶紧去药房取药。我说全家人,是因为门诊来人往往是三代同堂。我敢肯定这是中国家庭表达爱的方式,同时这样也可以避免一个人对医嘱理解不当,影响实施治疗方案。而且长辈的年龄和经验也可以帮助小辈判断医生的专业水准。
来我这看病的法国或英国妈妈恰好相反,也许是因为身居国外,家人不在身边,她们独自带着两个或三个孩子前来,总是忙得不亦乐乎。
新加坡家长,或有的香港家长,情况又不一样。随同前来的家人不多,但是家长的问题很多。医学中本身就存在很多的不定性,但是这种不定性在他们那很难找到位置。一切都必须是可测量的,可解释的,几乎到了机械化的地步。他们总是在礼貌安静中提出他们的疑问。我现在意识到我比较不容易满足我的新加坡病人,因为一般说来,我给出的答案总比他们提出的问题少。他们总是带着贴着整齐标签的小瓶子,那里面有备用的常用药,我总为他们的这种整洁有序所折服。
我见到的印度家长,大都体态放松,语气柔和。印度家长提出的问题简洁明了,我总是很高兴的给予回答,何况提问的人总是那么轻柔,那么礼貌。当我认为所有问题都问答完毕了,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爸爸总会打断我的话,并满怀歉意的说:“呃..医生,如果您同意,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当然了!没问题!但是现在我明白了,在我满以为可以结束的时候,我往往还要再等好一会儿才能和我的印度病人说再见!
比利时家长呢,很难说。可能和英国家长有些相似,他们不是那种很快容易焦虑的父母,要等到不医院。我不会鼓励家长为了芝麻大的事就来看医生,可是有的家长也的确潇洒得很!有些患儿家长来找我时,我知道那是因为孩子的确有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而且他们是在家等了几天后,才来看医生的。
我差点忘了,我常被一些中国家长问“倒”了,尤其是那些新患儿的家长。他们还不太了解我,不知道有些问题问了我也白问,因为我没有答案可给。
比如他们给我看孩子脸蛋,屁股上或者背上的一丝红色的小痕迹,对我说,医生,这个以前没有,是什么?我对他们说,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我知道每次这么说,他们可能认为我没用或无知(我倒很乐意接受),但是我总能自我安慰,学医时我不但学会了治疗疾病,也学会了尊重个体差异。问题是我的确没有答案可给,但是我会告诉他们我认为那个小痕迹不是个问题。
有时家长因为我不能给出一个黑白分明的答案,感觉很不舒服;大部分时候,他们自己也说,其实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我感觉在家长的眼里,我这个老外似乎有某种特别的天赋,可以鉴别一个芝麻大的包包的由来。可惜我常常得让他们失望,因为我通常只给出一个很普通的诊断:那就是个红包包而已。大部分时候,他们也会有礼貌的说,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那如果我真的有疑虑呢?我会拿起书本,我会上网,或者我会推荐他们去看一位同行,这样我们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
今天的这篇是娱乐篇,选自一年前出版的《孩子生病怎么办》,题目内容略有改动。时间真快,这本书在当当网上线也一年了,偶尔去看看,还保持着%的好评(